欢迎来到98聘
写一篇《温故1942观后感》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8-28 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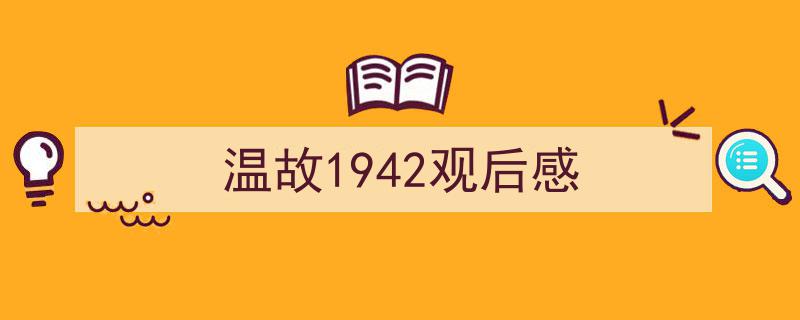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温故1942》的观后感作文,可以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让你的文章更深刻、更有条理:
1. "明确中心思想/核心感受:" 首先,你要清楚这部电影最让你触动的是什么?是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光辉与挣扎?历史的厚重感?还是导演的表达方式?确定一个核心观点或感受,作为你文章的灵魂。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和结构:" "切入点:" 可以从某个具体场景、人物、情节、画面、音乐或导演的采访/纪录片片段入手。例如,可以从主角(如白杨饰演的林祥福)的经历、某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如河南大饥荒)的呈现、电影独特的黑白影像风格等方面切入。 "结构:" 建议采用“总-分-总”的结构。 "开头(总):" 简要介绍电影背景(时代背景、剧情梗概,注意不要剧透关键情节),引出你的核心观点或感受,点明文章主题。 "主体(分):" 这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可以围绕你选择的切入点,分点、分层次地展开论述。每个段落可以: 描述电影中的某个具体细节、场景或人物塑造(结合原文,适当引用)。 分析这些细节/场景/人物所反映的主题
《一九四二》品读有感
《一九四二》品读有感前几天看了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又读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确实有点感受,不吐不快。先说电影。
电影的主题大家都知道两个字:饥饿!故事情节也很简单。1942年河南遭遇大旱,赤野千里,颗粒无收,国民党政府官员却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故意隐瞒真相,坚决不承认河南灾情,坚决不予救灾,且所征税款军粮等不得缓免减,更加重了河南灾情的蔓延,致使流民三千万无家可归,最终约有三百万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故事以腰缠万贯的土财主范殿元一家六口和长工拴柱为代表,讲了他们一家从遭匪、烧家、子亡,到外出躲灾、遭兵抢、到变成逃荒的灾民,再到因饥饿妻死、媳死、卖女、孙亡,最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的故事。看完电影的感受就是我想杀人!但电影中除了灾民,根本就没有人,都是畜生!上至委员长,下至小官小吏,再至日本人,一个个都是视人命如草芥的畜生。当然,那个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白修德是好人。再说下小说。小说主题是复盘历史!寻找当年亲身经历的老人,记录他们残存的记忆。找寻当年的史料,还原当时的现状。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有一个个老人的痛苦回忆,以及从能找到的不多的当年史料中的摘抄。其实不能称之为小说,实是1942之史记!感受:一是有颠覆性的认知收获。即1942年河南大灾真正的转折点居然是日本人在救灾,也就是说,是日本人的救灾才让三千万灾民的死亡数字最终定格在约三百万,否则极有可能是约五百万,甚至约八百万!因为旱灾之后是蝗灾,灾情一共持续了三年之久。二是不同意作者刘震云对《大公报》的评价。作者对《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主编王芸生颇有微词,并表示河南受灾人民不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报道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倒觉得应该大大感谢他们,最起码他们的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最起码通过他们的报道,全国人民才知道了河南受灾的事实。所以我们不但要感谢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也要感谢敢于第一个为灾民发声的《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主编王芸生!他们都应该永远被人铭记!特别是河南人,应该为他们建碑立庙,供奉香火!可惜,人们宁愿把钱扔给河南少林寺那个和尚养情妇养豪车,早已经没人记得是谁救了1942-1944年的河南人了,人们的记忆总是短暂且短视,可悲,可叹!正如你给了一个在沙漠中快渴死的人一瓶水,返回城市后他买了一瓶水还给你,说咱们两清了!三是在那种情形下,河南居然没有出现揭竿而起,确是令人称奇!四是有时候历史确是文学,有时候文学确是的的确确的历史,比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这篇。被遗忘的记忆《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笔下的历史叩问与人性救赎
一场被官方史书轻描淡写的大饥荒,一次被亲历者选择性遗忘的灾难,却在刘震云的笔下与冯小刚的镜头下,撕裂了历史的沉默幕布。1993年,刘震云在翻阅泛黄的档案与行走于河南延津的黄土路上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悖论:1942年河南饿死三百万人的惨剧,竟被民族记忆主动“抹除”。幸存者含糊地说“饿死人的年份多了”,地方志寥寥数笔带过,而当时的国际新闻是“宋美龄访美”与“斯大林格勒战役”。这种集体遗忘的荒诞性,催生了一部颠覆传统历史书写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当冯小刚在2012年将小说搬上银幕,历经19年审查波折的《一九四二》终成影像史诗。从文本到荧幕,这场关于饥饿、权力与人性的对话,完成了对民族灵魂的双重拷问。一、创作背景与历史真相:被遮蔽的“三百万人之死”刘震云的创作始于1990年的一次“偶然”。历史学者钱钢他整理河南大饥荒史料,在北京图书馆的尘埃中,他发现了触目惊心的数据:旱灾与蝗灾叠加,河南110个县受灾,灾民达三千万,官方统计饿死三百万人——相当于“建了三座奥斯维辛”。更令他震撼的是回乡采访的遭遇:亲历者如姥娘、花爪舅舅对1942年的记忆模糊不清,只喃喃道“民国三十一年?那年坏得很”。饥饿的根源远非天灾。小说以冷峻笔调揭示:蒋介石政府为保障军粮供应,在灾情最重时仍强征粮食;地方官员层层盘剥,甚至用“吃一次管七天”的伪科学欺骗灾民。而电影中一幕极具象征意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灾民啃食树皮的村庄里,看到省政府官员端上莲子羹、炸春卷的宴席菜单。权力与民生的割裂,在此刻鲜血淋漓。二、双线叙事与历史重构:小说与电影的互文性表达为打破单一历史话语的垄断,刘震云创造了“调查体小说”这一反传统形式。全书以双线交织推进:文献线:引入《时代周刊》报道、政府公文、日军战报等史料,拼凑出国际视角下的“大历史”;口述线:通过姥娘、范克俭舅舅等小人物的碎片记忆,还原吃观音土、卖儿卖女的“小历史”。电影则通过三条线索强化戏剧张力:1.灾民逃荒线(地主老范、花枝一家)——展现人性在极限环境下的异化与坚守;2.国民政府线(蒋介石、李培基)——揭露官僚系统对生命的漠视;3.记者白修德线——提供第三方人道主义视角。当小说中郭有运“因家人未死在一起而懊悔”的独白,化作电影里老东家目睹儿媳产子而死的长镜头,两种媒介共同完成了对历史痛感的具象化。三、权力批判与人性质问:从讽刺到救赎的升华刘震云擅用冷幽默解构权力荒诞。小说中写道:“县以上官员绝不会挨饿,性问题也解决得很好”;蒋介石官邸被形容为“堪比白宫”,而千里外的河南正上演人相食。这种尖锐讽刺在电影中被视觉化:重庆宴会厅水晶灯下觥筹交错,与河南雪地里僵硬的尸骸交叉剪辑。但作品并未止于黑暗。蒂姆·罗宾斯参演《一九四二》的理由点明内核:“它让人看到人性黑暗,也看到光明”。正如:小说结尾,老东家逆着人流折返,收养父母双亡的女婴——“叫一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电影中花枝为让孩子活命自卖为奴,临别将破棉裤换给丈夫的细节。这些微光印证了刘震云的话:“幽默背后是悲凉,而悲凉深处有慈悲”。四、语言艺术与民间记忆:方言、遗忘与历史重构刘震云摒弃华丽修辞,采用河南方言与白描手法唤醒土地的真实触感:“地裂得像小孩嘴,浇一瓢水滋滋冒烟”(小说)“饿死几十口?嗨,记不清了”(电影花爪舅舅对话)这种“土腥味”语言在电影中转化为延津方言对白与灰黄色调影像,构成对“官方普通话历史”的抵抗。更深刻的是对“遗忘机制”的揭示:当姥娘混淆1942年与其他灾年,当后代对三百万死亡数字无动于衷,刘震云指出——频繁的苦难使麻木成为生存本能。而小说与电影的价值,正是将统计学意义的“三百万”还原为一个个有名有姓的生命故事。五、从文字到影像的艰难旅程:十九年破壁之路王朔在1993年读完小说后疾呼:“小刚,这事你得干!”但这条改编之路竟长达十九年。剧本十次修改,多次因“暴露民族阴暗面”被驳回。冯小刚在自序中坦言:“每次搁置,都像心上被捅一刀”。为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电影新增两条关键处理:1.加入宗教元素:神父安西满的信仰崩塌与重建,隐喻苦难中的精神求索;2.强化幸存者叙事:老东家从地主到灾民的身份跌落,使观众得以代入历史。当徐帆饰演的妇女为不让孩子被卖为奴,含泪用扁担拍死亲生女儿的镜头震撼银幕(取材于真实口述),小说中“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不可预测性”终获影像证明。《温故一九四二》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用“无情节、无人物、无故事”的调查体撕开历史伤口(小说形式),更在于它拒绝让苦难沦为煽情素材。刘震云以克制的笔调书写饥饿,冯小刚用雪原长镜头凝视死亡——正如电影中逃荒队伍最终如黑点般消失在地平线上,所有呐喊归于沉寂,却留下永恒的诘问:当一个民族习惯遗忘痛苦,当权力依旧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谁能保证1942年不会重来?而小说结尾那句“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既是卑微的生存宣言,亦是对人性韧性的最高礼赞。在记忆与遗忘的拉锯战中,这部作品终将成为钉入历史骨髓的荆棘。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