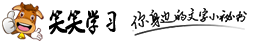欢迎来到98聘
东欧文学读书笔记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2-12 10:13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东欧文学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内容充实、见解独到且结构清晰:
1. "明确核心主题与范围 (Clarify Core Theme and Scope):" "选择焦点:" 东欧文学流派众多(如布拉格学派、耶鲁学派、波德加莱学派等),作家和作品浩如烟海。你需要明确你的读书笔记聚焦于哪个特定时期、流派、作家、作品,或者东欧文学某个普遍性主题(如历史创伤、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荒诞感等)。清晰的焦点是文章的基石。 "界定范围:" 是针对一部具体的小说/诗歌/戏剧,还是几部作品进行比较,或是概述某个作家的整体风格?明确范围有助于你控制论述的深度和广度。
2. "深入阅读与精读 (In-depth Reading and Close Reading):" "不止于情节:" 读书笔记不应仅仅是故事梗概的复述。要深入挖掘文本细节,包括语言风格(象征、隐喻、反讽)、叙事技巧(非线性叙事、视角切换)、人物塑造(心理刻画、典型性)、象征意象、结构安排等。 "记录关键点:" 在阅读过程中,勤做笔记,标记让你印象深刻的句子、段落、人物、情节转折、主题暗示
诺奖之后,我们还会想起东欧文学吗?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卢灿秋 记者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在中文世界广为流行并衍生出不同主语的谚语,最初因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次颁奖典礼发言上的引用而流传。
自80年代起,中国席卷过一场长久的发烧般的“昆德拉热”。他的大量作品被译介至中国,不同译本一次又一次出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作品为几代人所熟知。历史上中国读者与东欧文学曾有过紧密的关系,许多人现在仍能脱口念出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爱情与自由”。
然而,对于刚刚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以及他背后的东欧文学,中国读者却不甚了解。比如在讨论最初,大家弄反了这位诺奖获得者的名字与姓氏;相比他的书籍,更被人知道的是他参与编剧或由其作品改编的《都灵之马》与《撒坦探戈》等电影。在赫塔・米勒、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获得过诺奖的作家之外,其他东欧当代作家则甚少被关注。
我们好像已经站在了距离东欧文学很远的位置。
回顾东欧文学在中国的百余年译介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关注者一直将其当做一盏具有相似处境的棱镜,透过其去寻找自身的位置。这种关注现在仍然存在。在翻译作品多元、社会生活多元的当下,伴随着“东欧”概念逐渐模糊,过去集中在文学上的目光也弥散开来。不过,东欧作家的抗争与流亡经验以及被标注为“斯拉夫美学”的各种媒介产品依然在产生影响。
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或许在于提醒,那种对于命运、自由与记忆的思考,从来不是别处的故事。
从红色到蓝色
在动荡的百余年里,东欧文学与中国读者几经交织,它是如何成为一盏关照自身的棱镜的?
因为东欧国家深重的民族抗争历史及其与现代中国相似的处境,中国文人自19、20世纪之交便开始译介东欧文学。在20世纪初期,鲁迅与周作人对包含东欧文学在内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推广“立意在反抗”的外国文艺,发表了诸多介绍东欧文学的文章及译作,并影响了第二、三代译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关译介较为活跃。以文学研究会为核心力量的《新青年》杂志和《小说月报》是主要平台,茅盾、郑振铎、刘半农、冰心、许地山等许多作家参与其中,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更多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进入中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一几代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裴多菲的格言诗的译本便诞生于这个时期,由烈士殷夫翻译,1933年鲁迅将其引录至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
在建国初期,中国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密切,文艺界倡导学习与介绍苏联及新民主主主义国家文学。许多东欧文学作品被译入中国,例如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的《斧头》《倔强的驴子》、剧作家扬·路卡·卡拉伽列的《失去的信》、波兰作家普鲁斯的小说等,形成又一次热潮。
现在留在生长于六七十年代的读者印象里的东欧文学则来自八十年代的翻译热。彼时“走向世界”成为社会的主流叙事,文化环境相对开放,国内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文学,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也逐渐多了起来。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等作品以及来自东欧的电影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尤其是米兰·昆德拉,这位来自捷克的作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持续数年的“昆德拉热”,其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不朽》《玩笑》等至今仍具有广泛的知名度。米兰·昆德拉凭借他对政治与社会现状的反思与批判以及独特的写作方式——幽默、机智、对性爱的大量正面展示等,吸引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并影响了一代寻根与先锋作家。
关注的消退
从出版数据来看,目前对东欧文学的翻译数量较少,对作家及作品的关注有限,并且在作品出版上有较大时差。以拉斯洛为例,他在80年代就以《撒旦探戈》与《反抗的忧郁》成名,这两本书分别在2017年与2023年才进入中国文学市场。
那这一与东欧文学间“关系冷淡”的情形是在何时出现?又是因为什么呢?
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据《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告诉界面文化,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和东欧的文学和学术交流不畅,资料匮乏。在21世纪初期,对东欧文学的翻译出版总体上较八九十年代有所减少,这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受到国外作品版权限制有关。
其中,东欧文学的翻译断档问题是影响东欧文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大因素。国内匈牙利当代文学的主要译者余泽民告诉界面文化,这一状况已经持续二十年了。“从‘文革’开始之后,各个语言基本上都断了。(‘文革’结束后)有些老翻译在做,老翻译不做之后就没人了。”一方面是语言专业培养更注重应用翻译,另一方面是当下的社会氛围并不提倡阅读,无法有效培养文学翻译人才。“我完全是一个特例,我不是作为语言学生被培养出来的。我是遇到了80年代特别饥渴的时候,突然放开之后主动地大量阅读。即使我学医了,还是读文学的。”
关于“现在中国读者是否对东欧文学感到陌生”的问题,高兴认为不能说陌生,而是阅读选择更多元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学译介范围大幅拓宽,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译本。读者被不同的文学魅力吸引,他们的目光不再集中于东欧文学,还会关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文学作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社会生活的中心不再是文学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中心,80年代时,作家、翻译家、诗人会受到很多关注。但现在世界多元丰富,有音乐、美术等太多事物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读者对文学的关注,这是正常现象。”高兴说。
面对“拉斯洛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度和他的文学水平不相称”的评价,余泽民认为这是文学评价体系的原因:国内经常将书籍销售量与获奖情况作为其质量的衡量标准,这个尺度是有问题的。高兴也关注到了市场评价对东欧文学传播的影响:“出版界有时会受效益影响,往往等作家获大奖后才会关注、出版其作品,其实很多有潜力的作家早有优秀作品。”例如,余泽民早年就曾将拉斯洛的代表作推荐给中国出版社,但直到拉斯洛于2015年获得国际布克奖之后,他的作品才被逐渐译介到中国。
在社媒讨论方面,相比中国港台地区、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其他地区文学的bot账号,“中东欧文学bot”的粉丝数与其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差,并且在仅运营了两年后于2023年8月停止更新,也可看作东欧文学当下在中国受到关注鲜少的体现。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远离东欧文学了吗?
流亡与转移
在读书类bot中检索“东欧文学”,除了2018年诺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的《太古与其他的时间》和她的其他小说,评论区里经常提到的赫塔·米勒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以及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疼痛部》,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小有讨论。一些读者说,他们知道这些作品,但并不知道它们也可以属于东欧文学。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收录了赫塔·米勒的九篇散文,讲述她从罗马尼亚的小村庄“出走”到德国的故事。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1991年内战爆发后因公开反对战争与民族主义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于1993年被迫离开克罗地亚,后来定居荷兰。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在《疼痛部》中,她讲述了一个“一群来自于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没有身份的人,共同以一门灭绝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与文学”的故事。
这些经验都有关于流亡,这与“东欧”概念本身在逐渐变得模糊是同源的。
“东欧”并非一个稳定的地理实体,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与历史概念。它的形成根植于多重帝国历史的交错影响,现代意义上的“东欧”概念诞生于二战结束后,在冷战时期被苏联统治与西方视角重新界定。在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原东欧国家纷纷试图摆脱这一标签,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高兴认为,之所以依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和研究,是因为它们在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共同点,在文学定位上,现在称其为“中东欧文学”更为合适。
在余泽民看来,“东欧文学”的概念在今天仍然成立。“东欧国家很晚才加入欧盟与申根,有的还没有加入,那它们肯定保持着原来东欧历史的遗迹,还是很沉重的。”
赫塔·米勒与杜布拉夫卡近来受到的关注还反映了东欧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新情形。近四十年间,东欧当代作家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多是源自他们获得国际性奖项(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关注度也随对诺奖讨论的减少而跌落。而赫塔·米勒获得诺奖的时间是2009年,杜布拉夫卡更是不因获奖而受到国内读者关注。她们的作品均是在中文出版后,借由社交媒体的传播被更多读者看到,也因“女性”身份引起话题性讨论。
此外,国内对“东欧文学”的关注的解离还在“文学”上。
相比拉斯洛这位新晋诺奖得主难以进入的“火山岩浆般缓慢流淌”的复杂长句,关注者们更愿意走进的是电影版《撒旦探戈》——当然,它也因7小时的时长让人望而生畏。今年瑞典文学院给拉斯洛的颁奖词是“他那富有感染力与远见卓识的作品,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而“末日感”“末世感”是短视频平台中并不小众的标签。
这或许意味着大家对于东欧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喜好从文学转移到了其他媒介上,并且更多表现为一种亚文化,对从前多与意识形态绑定的东欧文化进行了反收编。现在在爱好者间流传的“东欧”更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名为Doomer的meme,具有阴郁、冷冽感的后朋克音乐,流行一时的音乐《布拉格广场》与《克罗地亚狂想曲》,废墟核影像,对历史及现实有深刻思考的游戏《极乐迪斯科》……
记忆与记录的使命感
纵向来看,基于相似的经历,中国关注者对于东欧文学的兴趣一直围绕着对自我存在的探寻而展开。20世纪上半叶是在民族生存焦虑中将其作为参照,试图从中获得振奋力量。80年代则是借这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受到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承认的作家,来思考如何在世界中找到中国文学的位置。当下,即使承载媒介发生了变化,大家受触动的“大厦倾倒”后的流亡与颓废感也是一种当代人共享的症候。
东欧文学能在百年来持续散发这样的影响,与东欧作家“记忆历史”的创作特点息息相关,这也使他们享有相当的国际声誉。
“匈牙利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一线的,尤其是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做历史的记忆者。”余泽民说,“在20世纪,二战和冷战是欧洲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匈牙利作家所写反映的就是这两个时期。比如凯尔泰斯写二战,拉斯洛写冷战时和冷战后,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写剧变时期的许多底层人物。东欧人所经历的跟西欧人完全不同,西欧人对冷战没有这么深刻的体验。这些体验本身给东欧人提供了文学素材,他们从经验里吸取养分,形成思想性。”
马利亚什·贝拉 著 余泽民 译
花城出版社 2016-6
先后有10位东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兴认为诺奖评委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共通性是直面苦难的勇气、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以及将文学当做抗衡灰暗和严酷现实的武器的方式。余泽民认为他们都具有坚韧性与纯文学的信念,在长期写作生涯中往往能够咬住一个主题越写越深,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他们思考的不是一个社会现象,他们是围绕着自己的哲学核心去组织素材。
具体来说,凯尔泰斯·伊姆雷关注集中营与大屠杀。他认为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始终与人类社会并存,即使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烧掉了,还有另外的集中营,可能还有没有围墙的集中营。拉斯洛四十年来一直在写人类困境,他通过冷战看人类的发展。他觉得人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无论社会表面多么光鲜,各种技术发展,但是人类都是从绝望到希望、从希望再绝望的轮回。“就像探戈一样,往前两步,往后两步。”
在记录历史之外,拉斯洛也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密切关注。在即将于国内出版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原版出版于2016年)译序中,余泽民写到这本书探讨了一些当下的社会问题,比如体制变革、难民危机、吉卜赛人问题、媒体不道德的运作方式等。比如他写一家报社收到了一封辱骂匈牙利人的非常犀利的匿名信,写一个人过马路,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难民。这些让人联想到距离不远的两起事件:2011年,犹太裔匈牙利作家阿科什·凯尔泰斯在媒体上发表对匈牙利的批评文章,遭到了匈牙利右翼势力的围攻与恐吓,最后流亡到加拿大;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匈牙利政府拒绝接收难民,约8000名难民被迫滞留在布达佩斯东站及周边街区。
如此,东欧作家从各自的视角书写历史,每个人的原创性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文学景观。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余泽民 译
理想国 2015-8
在“历史之重”与民族认同的创作主题之后,高兴谈到新一代东欧作家发生的变化。“现在很多有实力的东欧作家早就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题,更多书写‘存在’这个人类大主题。他们作品的背景往往是模糊的,人物具有某种符号意义,追求作品的普遍性,希望写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内容。在写作手法上,有‘跨界’‘杂糅’‘融合’的大倾向,作品会涉及心理学、哲学、音乐、地理学等多个领域,打破单一写法,也打破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比如托卡丘克就是百科全书式作家,她的作品融合了多种领域的知识。”
但是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东欧作家之外,目前知名度较小的中小作家仍面临着作品传播困境。“东欧很多国家的语言是非通用语言,比如捷克语使用者约1000万,波兰语约3000万,匈牙利语不到1000万,语言障碍影响了作品传播。很多东欧作家渴望作品被翻译,尤其是翻译成瑞典文,因为瑞典文是诺奖评委能直接阅读的语言。”
高兴观察到,现在东欧文学的传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比如昆德拉、米沃什这样的大作家几乎没有传播困扰,而中小语种作家仍受语言与出版资源限制。“不过,也有许多作家在努力,例如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卡尔塔雷斯库长期被视为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北马其顿作家戈采·斯米列夫斯基、罗马尼亚女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等,也凭借自身创作与国际奖项的助力,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
参考资料
宋炳辉.(2017).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玮婷.(2020).红蓝二重奏:学者聚焦东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402/c404090-31658637.html
高兴.(2020).21世纪东欧文学:复杂、夺目,边缘的光芒.中国作家网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826/c433142-31837844.html
姜妍.(2012).东欧文学 影响衰落源于译者断档.新京报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44439014430.html
Starosta, A. (2015). Form and Instability: Eastern Europe, Literature, Postimperial Difference(Vol. 2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徐鲁青,董子琪.(2023).昆德拉逝世:诺奖错过了他,读者不忘记他.界面文化
.https://mp.weixin.qq.com/s/0ePk5dJ9Lar9Bjt9mtE6fQ
潘文捷.(2017).沉寂二十余年,俄语文学为何再度成为读者们的宠儿?.界面文化
.https://mp.weixin.qq.com/s/xmM1XW96AWN5p5SNLEheyQ
“蓝色东欧”7年译介40余部中东欧文学作品,但还远远不够
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涉及海内外参展商2500多家,有1000多位中外出版人、作家和媒体人参加书展,多家出版社在图博会上介绍了他们的出版成果,其中较引人注意的就是对一些海外作品的引进,尤其是一些虽在国外享有盛名,但是因为语言隔阂在国内不为人知的作品,出版商和翻译家们也为丰富国内的文学市场作出诸多努力。
七部东欧作品引入中国
8月23日,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主办的“‘蓝色东欧’新书发布暨翻译家分享会”在北京图博会举行。
花城
“蓝色东欧”译丛是花城出版社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东欧文学专家高兴担任主编,计划引进20世纪以来东欧的百部文学杰作。2018年,是“蓝色东欧”启动的第七年,目前已经完成了40余部。此次,“蓝色东欧”译丛携七部新书参加北京图博会。
这七部作品分别为国内首次推出的匈牙利当代作家萨博·玛格达的作品,此次出版的为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壁画》和成名之作《鹿》,波兰最杰出的喻世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的短篇小说集《简短,但完整的故事》,以及二十世纪捷克文学巨匠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四部作品。其中,有赫拉巴尔巅峰时期之作《严密监视的列车》,同名电影获得一九六六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赫拉巴尔隐居之作《雪绒花的庆典》,赫拉巴尔致敬友谊之作《温柔的野蛮人》,以及赫拉巴尔晚年的情感私信《绝对恐惧:致杜卞卡》。赫拉巴尔一生作品众多,并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获得国内国际奖项达三十多个。
赫拉巴尔
“蓝色东欧”所涉及到众多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译丛所推作家均为享誉世界的东欧文学重要代表人物,汇集了米沃什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卡达莱、克里玛、赫贝特、扎加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家,同时聘请高兴、李玉民、余中先、易丽君、赵刚、余泽民、陆象淦、徐伟珠等翻译家担任丛书翻译,推出的作品90%为国内首次翻译引进。
“蓝色东欧”丛书主编——著名翻译家高兴就“蓝色东欧”译丛新书做了相关的介绍,“蓝色东欧”从选题缘起至今已经有十多年,这套丛书成功的关键在于聘请了国内外顶级的中东欧文学翻译家。他与译者嘉宾余泽民、徐伟珠、茅银辉针对东欧文学、东欧作家等话题进行了探讨、互动。余泽民也谈及中东欧文学与欧美文学完全不同,渗透着哲学性与生动的历史,对中国读者和作家来说更能触动人心。徐伟珠说翻译出版是一个团队工程,每一部经典译作都是共同努力的成果。茅银辉认为“蓝色东欧”凝聚了中青年翻译家的力量,激励了年轻人从事有意义但艰苦的文学翻译工作。
中国读者对于东欧文学向来很有热情,20世纪初,作家李石曾、鲁迅、周作人等就是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的先驱。翻译家们介绍,尽管过去我国译介了不少东欧文学作品,但总体上说远远不够,还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问题:译介不够系统,存在许多空白点等等,都使得东欧文学译介留下了诸多遗憾。
作家们共谈赫拉巴尔
8月23日下午,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了“北京遇上布拉格——在小酒馆里听到的赫拉巴尔”文学交流活动,活动主要介绍了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部赫拉巴尔的书。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生于奥匈帝国布尔诺附近的日德尼采,他一生创作实绩丰厚,身后结集成19卷合集,在捷克国内畅销。他的77种书,迄今以2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个国家发行,主要作品有《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底层的珍珠》和《甜甜的忧伤》等。赫拉巴尔的作品多数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与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同名的电影于1966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根据《售屋广告:我已不愿居住的房子》改编的电影《失翼灵雀》获1990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1997年2月3日,这位原本即将病愈出院的作家从医院五楼窗口坠落身亡。
《过于喧嚣的孤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目前已出版赫拉巴尔的作品八部,包括《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一缕秀发》《甜甜的忧伤》《时光静止的小城》《婚宴》《新生活》《林中小屋》,其中《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是他的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废纸回收站的打包工汉嘉,以他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了他三十五年间的生活。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他狂饮啤酒,“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以一个餐厅服务员蒂迪尔的打工经历,展示了捷克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变迁。这部作品体现出作家一贯的回忆录式“传记”创作风格,通篇描绘了旅馆、饭店、酒家、餐厅和私人会所的生活,处处流露出布拉格帅克式的幽默、揶揄和调侃。
赫拉巴尔集 《时光静止的小城》
赫拉巴尔集 《甜甜的忧伤》
谈到阅读赫拉巴尔小说的感受,邱华栋表示,“他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语调,这种语调,亲切、随意、幽默,第一句话就能把你带入他的小说,又在告诉你,随后有事发生。可以说,他的小说开口很小,进入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小说世界绵密、细致,写的是小人物的命运,折射的却是家国情怀与民族命运。另外,阅读赫拉巴尔的作品,常常能感受到他作品中带泪的笑和无可奈何的幽默感。”
赫拉巴尔文字中的亲切、随意、幽默深受捷克人的喜爱,捷克人说,米兰·昆德拉的文章过于深邃,读起来有沉重感;而赫拉巴尔则像是啤酒馆里坐在你桌子旁的熟人,将无数奇特的故事娓娓道来,幽默而富有哲理,这才是纯正的捷克味道。关于赫拉巴尔作品中的“幽默”特质,著名作家石一枫说,“赫拉巴尔以幽默的方式呈现苦难与荒诞,是东欧文学的传统,我们从《好兵帅克》就可以看到这种气息。我个人最喜欢赫拉巴尔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在这部作品中,他把宏大的事情写得轻松无比,而这种能力是许多作家都无法做到的。”
青年评论家季亚娅关注到赫拉巴尔笔下的小人物,她说,“赫拉巴尔写的全都是捷克的小人物,我们常常谈起他底层的珍珠,并拿来和我们的底层写作、知识分子到民间这些问题相比较。但赫拉巴尔的底层不完全是中国作家语境里的底层,他是中欧思想传统里长出来的花,是与波西米亚精神相联系的底层,一种与艺术创造紧密联系,甚至把生活艺术化,并从中寻找能量和爆发力的底层。法学博士赫拉巴尔底层游历的自我设计,与中国作家的到民间去构成遥远的对话与重影。”
谈及捷克文学和赫拉巴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示,“捷克或许是一个地理上的小国,在文学的国际版图上却绝对是一等一的大国。哈谢克、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塞弗尔特、伊凡·克里玛,当然还有赫拉巴尔,这些名字足以让捷克文学置身于世界文学的高峰地位。赫拉巴尔之所以迷人,不只在于他作品的忧伤而孤傲的抒情气质,不只在于他作品的那些身居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饱经患难而快乐纯净的珍珠般光泽,也不只在于他以艺术与诗的美好,以诙谐嘲戏的姿态对抗平庸生活的倔强坚韧,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更是一个迷人的存在,提示我们,一个艺术家,他的生活是如何与他的创作浑然一体,互相生发。对于赫拉巴尔,爱上他和爱上他的作品简直就是一件事。”
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北京出版集团在2015年就成立了“‘十月’作家居住地·布拉格”项目,鼓励中国作家前往布拉格体验、交流、写作,目前,余华、苏童、叶广芩、吴雨初、马原等中国著名作家都曾前往布拉格居住写作,为中国与捷克的文化交流创造了鲜活的平台,也更为有效地推介中国优秀作品在捷克的传播。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