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98聘
推荐《受戒读书笔记300》相关写作范文范例(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15 1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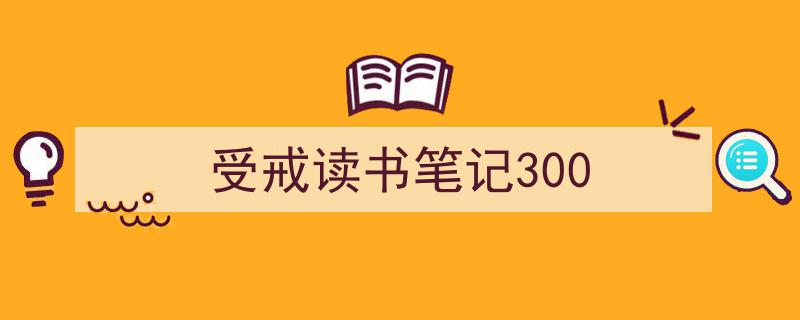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受戒》的读书笔记,大约300字,并附上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受戒》读书笔记"
汪曾祺的《受戒》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描绘了乡村生活的淳朴与美好。故事以一个外乡人闯入古寺,与农家少女小英子相识相知为主线,展现了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和纯真无邪的乡村爱情。
小英子是本书的灵魂人物,她活泼可爱,心灵手巧,对生活充满热情。她与明海之间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相伴,如涓涓细流,纯净而美好。汪曾祺用细腻的笔触,将小英子对明海的喜爱,明海对小英子的珍视,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
《受戒》的语言简洁明快,却富有韵味,充满了乡土气息。汪曾祺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和乡村的风貌。例如,对小英子学做香炉的描写,既生动又传神,展现了小英子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善良。
读完《受戒》,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宁静美好的乡村,感受到了纯真爱情的美好和乡村生活的淳朴。这本书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也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读书笔记—《受戒》《哭小弟》
汪曾祺(1920——1997),生于江苏高邮。代表作有小说集《邂逅集》,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等。
《受戒》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描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北小镇上发生的一段风流韵事。作家以当地和尚为题材,以诙谐而富有情趣的笔触,描绘了小小的“荸荠庵”内形形色色的和尚和庵外居民的风土人情。通过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描写了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表达了对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也含蓄地表达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和批判。 《受戒》在问题风格上追求小说与散文、诗歌的融合,淡化情节和人物性格心理,将散文笔调和诗歌的意境营造的手法引入小说的创作,以纯朴淡雅的语言,大量的风俗描写,呈现出一幅
原始淳朴的南方水箱生活的诗意化图景,形成一种清新独特的田园抒情风格。
小说平淡含蓄的方式对主题的表达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做情节的中心或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出现穿插成分:当和尚的风俗、荸荠庵里的生活、英子一家的生活、海明同英子一家的关系等。虽然枝节众多,但是小说的叙事却曲尽自然,放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流动的。文中许多细节描写刻画得纤毫毕现、贴切自然,富有诗意。文章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
作品风格淳朴、富于幽默感。行文好像不动声色而又情深意浓,描绘似乎不甚经意而美丑自见。整篇小说,藏庄严于诙谐之内,寓绚丽与朴素之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语言简洁犀利明快,含蓄风趣生动,极富个性色彩和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得力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透露出他的身份,表现出他的性格特点。
叙述从容、意境优美、寓意含蓄的艺术特点:本篇以回忆的视角展开叙写,时间和空间目的地距离使作者获得了一种从容的叙述心态。作者显然很注意叙述文件的纯静,还注意营造优美的意境,从而强化情感的抒发力度。精致之处更主要还是体现在含而不露的哀愁赋予了整篇散文一种内在的和谐;加强了作品那从容舒缓的叙述文体的抒情意味,使它能在不知不觉中拨动了读者灵魂深处的心弦。
《哭小弟》作者宗璞,原名冯钟璞,生于北京,原籍河南唐河,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爱女,幼承家学,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红豆》、散文集《丁香结》,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部曲《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等。
作者的弟弟,冯钟越,飞机结构强度专家,为我国的航空科研事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然而英年早逝却让人唏嘘,更让至亲的姐姐痛彻心扉。散文这一文学样式,天性自由随意,但真情实感却是其灵魂与生命力的所在。这篇悼念之作,就是以真挚的情感(围绕一个“哭”字),串联起小弟童年,工作和去世时的往事,作者在写作中结合细节描写和侧面烘托等手法,前者如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后者则体现通过周围人的反应,回忆来凸显小弟的献身精神。
作者在哀悼中执笔,却并未笔法纷乱,对小弟的追忆主要集中其卓越业绩,尤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长期坚持在艰苦条件下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作者并未让情感泛滥,以一句“小弟我不哭”!收尾,再将哀痛深埋心底的同时,将对小弟的哀悼发展到了与小弟有着同样“迟开而早谢”、“壮志未酬身先死”命运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悼念,“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凝聚着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及充溢着深广的人文人性关怀,也由此升华的主题。
散文风格独特,风韵别致,凝重而不刻板,深沉且又清新,华美典雅却以坚毅正直为骨,毫无奢靡谄媚之气,具有卓然异趣的艺术魅力。突破了一贯的节制蕴藉,激情充溢,长期而切身的大哀大痛,大波大澜,“血泪相合”,一涌而下,自然地从笔底流泻出来。文章寓抒情、议论于叙事之中,准确生动,简洁干练。
汪曾祺先生的偶然与必然
著名作家汪曾祺。
人的一生中,从循序发展与不断递进的规律来看,尽管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比如遗传基因、性情爱好、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以及成长环境等,都会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但是,也往往充满着一定的偶然性,特别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够决定人生的走向或发展目标。据汪曾祺先生自述,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义无反顾地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在日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这两部书所产生的影响。
1937年暑假后,日军攻占了江阴,隔江相望的高邮也处于危急之中。此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终止学业,作别母校回到家乡以躲避战火。不久,国军战局失利,人心惶惶,于是他又随着祖父和父亲,到距离县城稍远一些的农村庵赵庄避难,一住就是半年多时间。为了打发这段枯寂难耐的日子,汪曾祺挑选了两部文学作品随身携带,一部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部是《沈从文小说选》。从《猎人笔记》中,他认识到了俄国农奴主的残暴和农奴们遭遇的悲惨;当然,俄国庄园的日常生活、俄罗斯壮美的自然风光等,也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在阅读沈从文小说的过程中,特别在意的就是著者塑造的一系列农民、水手、小业主、强盗以及社会中的诸多下层妇女的人物形象。他觉得这些人物血肉丰满,口吻毕肖,如临三步,呼之欲出。他赞赏小说语言的生动、笔墨的朴素,时常被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近乎原始生存状态的矫健与力量所吸引,又常常沉醉于小说中描绘出的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与古朴有趣的风土人情。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他和著者的情感距离。小说中隐隐流露出来的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温爱之情,也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心扉,从中发现了作品的美与诗意,于是,对于著者及其作品便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认同感。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阅读感受讲给祖父听,讲给父亲听。祖父和父亲受到汪曾祺情绪的感染,也饶有兴趣地开始捧读起沈从文的小说来。正是沈从文的小说,给他们焦躁不安的避难生活打开了一片澄明的世界。小说中对湘西山民哀乐故事的娓娓述说和旖旎风光的细腻描绘,完全不同于他们早已习惯了的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尤其新颖而别致。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先生禁不住感慨道:读了沈先生的小说,我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在研究了汪曾祺人生发展的轨迹之后,完全可以说,庵赵庄避难生活中的恣意阅读,对他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沈从文不仅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也成为了文学创作时所刻意追寻的美学坐标。在战火四起、国土沦丧、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圣祥的声音在向他发出召唤:挥别故土,远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于是,他由上海经香港,绕道越南,然后再改乘火车,翻越隘隘关山,战胜恶性疟疾,九死一生,历尽艰难,终于跨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门槛,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在《自报家门》一文中曾深情地说:“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指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前是想到的。”
岁月易逝,山河有情。四十多年之后,当汪曾祺根据庵赵庄避难生活的这段人生经历,以邻家少女大英子朦胧而美好的情感故事为蓝本,着意创作出了《受戒》这篇小说,一经发表,文坛震动,人们忽然发现小说创作除了“高大全”“红娘子”等题材之外,还能够从诸如明海、小英子等凡人小事中,挖掘出健康的人性与美好的情感!当时,人们不禁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汪曾祺晚年曾撰文回忆说:“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