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98聘
写作《门口改造申请书》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15 1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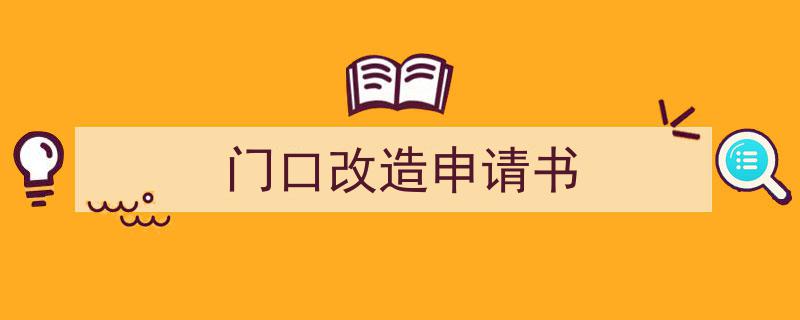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撰写门口改造申请书时应注意的事项的文章,希望能帮助你:
"精心撰写门口改造申请书,注意事项不可少"
随着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环境进行改善的需求日益增长。家门口作为我们进出住宅的第一道屏障,其外观、功能或安全性的提升,往往能显著提升居住体验和社区形象。因此,申请改造门口成为许多业主的合理诉求。然而,一份成功且顺利获得批准的申请书,并非简单的几句话就能概括。撰写时,若能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将大大增加申请成功的几率:
"一、 明确申请主体与事由,理由充分"
"清晰的身份说明:" 申请书必须明确写清楚申请人是谁,是整个楼栋的业主,还是特定单元的业主。如果是集体申请,最好能附上业主代表签字或盖章的证明。清晰的主体身份是申请有效的前提。 "具体改造事由:" 简洁明了地说明为什么要进行改造。是存在安全隐患(如台阶过高、地面湿滑、照明不足),影响功能使用(如快递柜/信箱位置不便、缺乏无障碍设施),还是与周边环境不协调,影响美观?理由需要具体、真实,具有说服力,能让审批方理解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 详细描述现状与问题,有据可依"
"客观描述现状:" 详细、客观地描述当前
困于斗室,或是走向人群——一根盲杖背后的500万次抉择
“叮”的一声,电梯停下,门一打开,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和敲击声。住户们频频回头,看着这群手里拿着盲杖的年轻人。
王梦瑶握紧盲杖,深呼了一口气。今天,她的任务是要自己走到商场,找到一间指定的打卡店铺。这是她失明后第一次独立走这么远,眼前只有一片漆黑,路上都是未知。“我还真有点……慌。”她低声嘟囔。陪同保障安全的志愿者阿姨伸手拍了拍她的背,轻轻抱了她一下,柔声安慰,“没事的。”
她参加的是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以下简称:金盲杖)的出行课。学员们聚在一起,只学一件事:拿起盲杖独立出行。
10月15日,是第42个国际盲人节。在中国,有超过1800万视障者,其中大约500万人因重度障碍,被困在家门以内,出行几乎完全依赖亲友。导盲犬稀少且训练成本高昂,远无法满足需求。相比之下,一根盲杖,成了他们最普惠,也最直接的选择。
但真正敢用盲杖走上街道的人并不多。他们受困于家人的不放心,无障碍设施的占用,更主要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坎。正如金盲杖发起人杨青风所说,许多盲人认为拿起盲杖是一件羞耻的事,它不只是工具,也是一种“标签”,意味着失明这件事,暴露在外人视线中。
尽管如此,这一次,他们还是决定试着拿起盲杖,走出去。
金盲杖的学员拿上盲杖,走上街头。新京报记者 徐鸣 摄
让所有伪装失效
直到30岁,在独立出行的第一堂课上,王春焱才第一次握起盲杖。
那天,她戴着运动相机记录学习过程,化了精致的妆容,却又用口罩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到老师带着学员出门实践时,大家一个接一个走出楼道。光线骤然强烈,他们走到了街道上。
她看不见路人怎样看自己,但想象中满是回头的异样目光。她的手不知往哪放,一会儿叉着腰,一会儿捋头发。最别扭的是那根盲杖,被她像握毛笔似的杵在身前,不肯伸出去,更不肯在地上敲出声响。
她说,拿着盲杖让她感觉“羞得很,像扒了一层皮”。平日里,她常被人夸好看,总是粉底服帖、戴着假睫毛。吃完东西,她一定会补妆,先用纸巾轻轻按掉浮粉,再补上唇釉,小心摸索着旋紧瓶口。在她的想象中,拿盲杖意味着身体要“往前探”,姿态显得畏缩、难看。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随之而来的宣告——她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她患有先天眼病。小学时还能勉强在第一排看清黑板上的大字,后来视力逐渐下降,生活无法自理,由家人陪读艺校学音乐。如今,她眼前只剩下一点光感。
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视力状况,她总结出一套“窍门”:即使独自在家,想拿桌上的杯子,也要“看”着去拿;与人交谈时,顺着声音方向“对视”;出门时,不让家人搀扶,只轻轻挽住家人的胳膊,保持一定距离。外出驻唱时,她从未向老板透露自己是盲人。每当需要调音,她也不说自己看不见,只解释自己不会操作。
但盲杖,会让所有这些精心构建的伪装,瞬间失效。
起初,她只愿意接受导盲犬,因为那样更像依偎着家人,不会显得“可怜”。可提交申请后,她得知最快也要等一年。她只好转为选择盲杖,下单买下人生第一根盲杖后,却又将它放在家里,一个半月都不肯带出门。直到在家人的鼓励下,她才带着它走进了出行课。
和凯凯的盲杖,则在包里搁置了16年。2008年,他刚到北京的按摩店上班,从残联领到人生第一根伸缩式盲杖。他把它收进包里,偶尔带出门,从未真正使用。
他总能找到理由逃避。出门打车,花点钱图方便;和朋友在一起,总有人领着,不必自己摸索。
和王春焱一样,他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视力状况。在最在乎的人面前,这种掩饰尤为强烈。想起第一次去见对象的父母,他事先反复向女友打听,了解她家客厅和卫生间的布局,想把每个方位记在心里,好不用盲杖行走。可真当身处她家时,他一整天都不敢离开沙发,只敢抿两口水,怕摸不到卫生间的位置。趁对方父母不在时,他立马拉着女友,把墙的边角、门的位置全摸了一遍。
虽然女友父母早已知道他是盲人,但在他看来,一旦拿出盲杖,“印象分就全部扣光了。”他怕那根伸出去的棍子,坐实了他是一个需要长期被照顾的“累赘”。
这种精心的掩饰,在独处时常常显得徒劳。他也明白,那不过是自我安慰,“看不见的样子,谁不知道呢?”念头至此,童年的记忆便会浮现。那时在盲校,和朋友拿着白蜡木棍胡乱在地上敲,走街串巷。那时,他心里还没有生长出“羞耻”这根刺,那根“木头棍子”只是帮他走得更远的伙伴,简单而纯粹。
可当他真正下定决心,想找回那份简单的勇气时,却常常发现,最先伸过来拦住他的,不是马路牙子,而是家人的手臂。对许多盲人来说,拿起盲杖不仅要跨过自己的心理障碍,还要冲破家人的“包围”。
曾在金盲杖实习的枭枭记得,一次训练中,一位家长死死守在孩子身边,工作人员劝了许久也不肯放手。也有学员的丈夫态度坚决地说,“这是我老婆,她该怎么做我来决定。”
学员王梦瑶的感受类似,家人的“包围”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每当她想拿起盲杖出门,总会听到家人说“今天太热别出去了”“下雨了,让人送你吧”。这些夹杂着阻挠的关心,一旦升级为争执,就会变成指责,“你眼神不好还出去干嘛?逞什么能?”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一句话是,“你跟我们出门拿着盲杖,路上那些怪怪的眼神你又看不见,可都是我们受着。”这让她对盲杖的抵触感更深。她常开玩笑说,要是能有一门专门为盲人家属开设的心理辅导课,该多好。
学员们拿着盲杖,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乘坐地铁。新京报记者 徐鸣 摄
困在屋里的渴望
有了想见的人,即使对盲杖再排斥,王梦瑶也要拿起它,走出家门。
两年前,中专毕业前一个月,学校以单眼视力0.3,无法考教师资格证为由,将她退学。当时,她另一只眼已经完全失明。在校期间,她正常学习声乐,期待毕业后成为音乐老师。原本按照学制,4年后她会直升大专、本科。退学后,她在家休息一年,那只0.3视力的眼睛突然视网膜脱落。最终医生判定无法治疗,她彻底失明。
被退学、手术和失明接连打击后,她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只剩下麻木。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如何熬过这一天。躺在床上难受,换到沙发上更难受。她不想出门,苦闷不知道向谁诉说。麻木偶尔会沸腾成愤懑,她抱怨命运,质问学校的不公。家人有时也忍受不了她的状态,激烈的争吵时常爆发。
唯一的盼头,就是周五的晚上。朋友会带她去足球场踢球——这是她失明前最喜欢的运动。她早早换好运动鞋,等着那声敲门。球场上,朋友把球放到她脚边,她就铆足劲踢,不管是否对准球门。射门前的那几步助跑,是她仅存的奔跑时刻。偶尔,听到球钻入网窝的声音,她会欢呼:“今天走大运咯!”
但这短暂的宣泄,缓解不了太多压抑和孤独。和失明前的朋友聚会,她们聊着最新的影视剧,她一无所知,也看不了,一句话都插不进去。一起出去玩,即使朋友们都说不介意,她也总感觉自己是那个被小心照顾的“麻烦”。渐渐地,她收回了和朋友同行的脚步。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家人为她报名盲人电脑课程之后。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真正点燃她的,是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先天失明的朋友。王梦瑶听着对方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如何独自坐公交、逛公园,她终于愿意承认,原来失明后的生活也可以这样过——不是只能等待和依赖,而是可以主动去探索、拥有。一团被压抑已久的火,仿佛突然找到了氧气,“突然有了希望。”
她开始试探着出门,为此报名了学盲杖的课程。即便没有课,她也会早早起床,收拾好书包,独自敲着盲杖前往地铁站,去找正在上课的朋友。周末,她也会去找住在家南边的朋友,那条路线她已经走得十分熟练。
每次见面,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和家人的矛盾、生活的巨大变化、对被学校劝退的不服……这些苦恼,她的朋友都能理解。两人会一起敲着盲杖去打卡各个想玩的地方,有时逛商场、吃火锅。有时什么也不做,只为见面,“哪怕只是坐在路边吹吹风。”
家人带她去山西看望长辈,她也会悄悄把盲杖放进行李包里,计划用盲杖提前练习去打卡地的路线。她生活中又多了一个愿望:等和朋友把盲杖练得更好,两人再去山西旅游。
每个人决定拿起盲杖的动力各不相同。大二那年,杨文博的眼睛被检查出问题,短期内生活尚能自理,但医生预告几年后可能完全失明。他不得不暂停学业,接受治疗。之后,他的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时而为未来担忧焦虑,时而紧紧抓住仍可看见的当下,沉浸在自己热衷的集换式卡牌游戏中——那是一项高度依赖视力的爱好。
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医生的预判降临,他失明了。之前,他海外名校毕业,做着自己喜欢又擅长的工作;失明后,却失业在家。巨大的落差让他陷入混乱:迷茫、恐慌,想找出路却无从下手。他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由行动,也还没学会使用读屏软件,整日坐在黑暗里,把手机像烙煎饼一样在手里翻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交谈中,“自我”是杨文博反复提及的词。失明后,许多事情必须依赖家人,家人是否方便是首要考虑的,“我想”“我需要”往往只能排在最后。他一贯独立,不习惯这种状态。而当看到许多盲人被局限在推拿这一类固定职业时,他更感到恐慌。似乎“视力”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前行的路,也抹去了所有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为了有更多选择,他开始学着使用盲杖出行,也逐渐接触读屏软件。
与杨文博相同,和凯凯拿起盲杖出于现实考虑,在他的想象中,有一条具体的、学会使用盲杖后的路。他在北京做了17年按摩师,每天晚上11点送走顾客、收拾好床铺后,就直接躺在按摩床上休息。对他而言,如果能把盲杖练熟,独立出行,就能去社区医院工作,不仅收入更高,下班时间也能提前好几个小时。
他也明白,不能一辈子待在大城市的推拿店,年纪大了可能逐渐被市场淘汰。他想将来回老家开按摩店。之前他也开过店,一旦需要出门买东西或交费,得依赖视力好的前台,前台休息时,事情只能拖着。
杨青风说,来学出行的学员,有的是为接送孩子放学,想多陪伴孩子。更多的,是因为生计。能自己出门,工作机会多一些。盲人不愿、不会用盲杖,无法独自出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职业上只能选择推拿——吃住都在店里,不要求出行能力。
他说,学用盲杖表面是解决出行问题,实际是就业、人际、心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只要走出家门,就有与人交流碰撞的机会”。
学员们学习如何过十字路口,需要挥舞手臂提醒来往车辆。新京报记者 徐鸣 摄
变长的“手臂”
当仗尖在盲道上滑过,手里传来一阵阵细碎震动,就像摸着纸扇的褶皱,一道一道起伏。水泥路是“哒哒”的坚实反馈;商场光洁的瓷砖则回声清脆,提醒他已进入室内;一旦声音变得沉闷,反馈变得柔软且带有一点回力——“是地毯,前面可能是电梯厅或者影院”;泥土地面与地毯类似,但杖尖提起时会带点阻力,好像被吸住了一瞬。
盲杖不仅仅是一根“棍子”,而是变长了的“手臂”,曾在金盲杖授课的郭万成形容。
有时,郭万成会带学员去河边,教他们识别水域的危险。盲杖一探进水里,手上立刻是一种“空了一下”的失重感,没有落点,杖尖在水中摇摆。
声音的反馈来得比触觉稍稍滞后,但也是勾画脑海地图的关键信息。在专门的“回声课”上,学员学着通过回声速度的微小差别,来判断与障碍物的远近。他们在身侧敲击盲杖,然后朝着墙壁一步步走近。耳边传来“哒——哒——”声,随着与墙的距离缩短,回声返得更快,仿佛有人在眼前应答。
不同高度与材质的障碍物,回声也各异。如果面前是一辆轿车,回声会快速、平面地反弹回来,感觉像一堵矮墙立在正前方;如果是一棵行道树,部分声音会从较低处返回,另一部分则会消散在空中,形成一种“上半空荡,下半实在”的听感;若是走到一栋高楼脚下,声音仿佛撞上一面巨大的屏障,整个被压下来,面前的空气都像被堵住。
金属面板的回响最让人警觉,盲杖一点,声音陡然尖锐,手里传来“空心”的反馈,不再像地面那样踏实。那往往意味着电扶梯口就在前方,学员需要立刻把盲杖竖起,贴紧身体,以免绊到路人,再小心踏上阶梯。
除了杖声,嗅觉和肌肤感受到的信号同样能导航。风从脸颊擦过,耳边有水流声,便是走到了桥上;阳光突然大面积扑在脸上,就是出了地铁站;若光线骤然消失,手还能摸到冰凉的铁柱子,旁边是一块平整的广告牌,那就是公交站。
商场入口的场景尤其容易辨认,脚下坚硬的石砖突然变成松软的地毯,头顶吹来猛烈的风幕机气流。若这时再闻到一股二手烟味,判断就更加确定——商场禁烟,有人抽烟大概率是门口。在盲道上敲到一辆接一辆的共享单车,这是阻碍,也是线索,意味着离地铁站不远。
阳光、气味、风,这些所有人都看不见的东西,他们能敏感捕捉。
然而,走在路上,不仅要面对障碍物,还有内心的恐惧。杨文博有一次在小区附近“鬼打墙”,盲杖不断敲到相同的砖和标志物,始终走不出去。敲击的节奏越来越快,心里也越来越急。太过慌张,半小时过去,他才意识到自己带了手机,可以打电话求助。回到家后,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只感到手腕酸麻。
出门,也意味着面对路人的目光。一次训练后,一名学员哭着回到教室,说刚刚路人硬塞给他200元钱,他受不了那种耻感。另一位学员打趣,“下次你不要,给我花”。气氛立刻轻快起来,大家笑成一团。
每次训练回到教室,学员们都会先交换一路上捕捉到的细节线索。很快,话题就转到盲杖上,“你的杖头磨得快吗?”“用折叠的还是伸缩的?”“滚轮头是不是更顺手?”
再往下,谈话会忽然打开,“如果眼睛能看见,你最想做什么?”有人说要去学开车,有人想真正坐在球场里看一场比赛,还有人惦记着去杭州,那是他在失明前差点就到达的地方。
学员将盲杖竖起,乘坐扶梯。新京报记者 徐鸣 摄
新世界
郭万成记得,最初带学员外出训练时,常常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人边走边抽烟,有人戴着耳机听歌,有人聊个不停。他一次次提醒,“专心拿着盲杖去感受。”可学员们仍我行我素。终于他忍不住了,“我和你们一样,也看不见。为什么你们就不肯好好学?”
那一刻,队伍安静下来。回程时,之前抽烟的学员主动找到他道歉,“我以为你是明眼人,觉得你体会不了我的感受,凭什么教我。可你也是盲人,还能在前面带我们走,我是不是也能走这么好?”
“大家是被一群‘能走’的盲人吸引了。”郭万成说。
有学员不愿意拿盲杖,他就问,“你会觉得用筷子是一件羞耻的事吗?”学员说,“不一样啊,用筷子的人多,用盲杖的少。”他追问,“那世界上用筷子的人是少数吧?下雨打伞的人多,穿雨衣的少,穿雨衣就丢脸了吗?”在课堂上,郭万成常用一些比喻来让学员转变抵触心理。
慢慢地,转变开始发生。
王春焱的变化最直观。她最大的进步,不是走得更稳,而是终于摘下了口罩。她感官敏锐,盲杖在她手里轻巧得像一条引路绳,几乎从不被障碍物绊住。第一次独自出行后,她惊喜地发现,一个人走路,“原来这么自由。”盲杖不再是心理负担,而成了日常的一部分。她每次用完,都会拿湿纸巾细细擦拭,收拾整齐放进包里,还曾打算买点小饰品,把杖头装饰一番。
回想过去,她说后悔没有早点学习出行,活得太封闭,“感觉错过了很多机会。”更让她觉得遗憾的是,她甚至无法意识到具体错过了什么。如今,她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主动展示“视障女孩”的标签,记录学盲杖的过程与生活日常。
杨文博则在盲杖里找到了久违的乐趣。对他来说,每次出行都像一场沉浸式的“找不同”游戏。他会用失明前的记忆,与现在的触觉和听觉一一对照。曾经,他走路时总是低头玩手机,无暇他顾。如今,他能听出哪家店铺可能关门倒闭了,闻出鱼腥味判断家门口市集出摊时间,经过时听到爷爷奶奶们在买菜时讨价还价。他用盲杖在脑海中绘制地图,街边多了一堵墙、少了一棵树,他都能察觉。
一次,他在家门口过一条熟悉的马路。之前,每次经过,都有志愿者拿着喇叭放着引导语,上前来帮助他。这次工作人员消失了。直到盲杖触到一个铁质的东西——他摸了摸,表面粗糙,方形,里面还飘出了冷气,传出文明交通的宣讲声。他特意围着“它”转了几圈,然后猜出,这是马路边新建的岗亭。熟悉中的微小“背叛”让他心里莫名涌起新奇、兴奋的感觉,“我好像又找到了些什么新东西”。
后来,他带着盲杖去了国家博物馆。失明前,他也逛过博物馆,但只是拍照打卡。那次,他租了讲解器,一边听,一边捕捉周围人的议论,然后想象展品的样子。等走到文创周边区,他再用手触摸一比一复刻的展品——材质和外形,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新世界”的冲击让他意识到,自己依旧能“看见”,只是换了一种更丰富的方式。
但改变并非直线向前。杨青风说,很多时候,出行的改变更像是一种“螺旋”,时而上升,时而下沉。有人遇到挫折,就退回到家中,困在那里。“就像在水里扑腾,浮上来,沉下去,全靠自己。”
也有学员在训练营毫无心理负担地使用盲杖行走,但仍不愿在家附近200米内拿起它。郭万成坦言,选择来到金盲杖的学员,未必完全认同自己的盲人身份。但即便如此,能够选择拿起盲杖,就意味着改变的开始。
至少,大家不时能线上聊聊天,知道身边还有同行者,还能互相提醒:“拿起了,就别再把它放下。”
学员们正在用手触摸交叉路口示意图,了解红绿灯、车道和斑马线的方位,一旁是收缩起来的盲杖。新京报记者 徐鸣 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梦瑶、枭枭、杨文博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徐鸣
编辑 杨海 校对 吴兴发
“充电刺客”出没!北京部分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价格真挺乱
近年来,北京市陆续发布了涉及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的地方标准及多个政策文件,今年9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书,重申价费分离、明码标价、居民住宅小区内按民用电价收费等要求。
然而近期一些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至今仍存在收取高价电费和混合收取电费、服务费等情况。政府的相关要求已经十分明确,为何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仍有“刺客”?记者展开走访调查。
按照商用电价收费
只因没有民电接口
家住通州区果园西小区的张先生近日反映,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按1.2元/度的商业用电价格向居民收取电费,而根据政府规定,本应按照居民生活用电的标准(即0.5103元/度)收取。由于认为充电价格过高,一些居民在单元门门口飞线充电,安全隐患不小。
10月4日记者来到果园西小区,该小区30余个充电桩集中设置于小区南侧的一处车棚内,这里既有充满即走的临时充电区,也有可以长期停放的固定充电区。这两处充电区内的充电桩分别由“驴充充”和“万威智充”两家公司安装和运营。记者分别扫取充电桩上的二维码后看到,两家公司在计费标准一栏都明确标注着电费为1.2元/度。车棚南侧的墙上张贴着充电站的收费标准,其中在电费一栏不仅写着“1.2元/度”,旁边还专门注明该价格为“商业电价”。
果园西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电费按商业电价收取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小区北侧距离车棚较远的部分居民楼的确存在飞线充电的情况。当天中午时分,小区10号楼前,多条电线从楼上甩下,三辆电动自行车、一辆电动三轮车以及一辆京B号牌的四轮代步车正在楼前飞线充电。其中一位车主还在单元门旁的外墙上装了一个小铁箱,从楼上甩下的电线、插线板以及电动车的变压器都被锁在该铁箱内。类似的情况在小区3号楼同样存在,该楼多个单元的外墙上安装了木质或不锈钢材质的小箱子,里面装有插线板和插座。采访中有居民表示,小区南侧的充电车棚收费高且距离远,因此才拉线在家门口充电。
果园西小区有居民在单元门外自行安装了“飞线充电箱”
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小区内充电桩电费高的问题由来已久,之前自己也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但都没能得到解决。“东边的果园225号院9号楼与我们小区就隔着一条六七米宽的小马路,他们的充电桩就是按0.5103元/度收费,每次充电的价格比我们这边便宜不少。”
随后记者就该小区充电收费较高的问题联系到属地果园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一问题此前街道和社区都找过供电部门,但一番查看下来发现整个小区周边都没有能为车棚接入民用电的接口,因此现阶段充电只能按商业用电价格。目前果园西小区周边还有多个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仍按商业用电价格收费,仅有果园225号院9号楼因为是从小区门房拉的线,所以享受到了民用电的价格。“现在要想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电价高的问题,可能需要电力部门在周边增设一些接口。这一情况已经上报给了街道,后续看看能否有解决的办法。”
小区没取得房产证
无法享受民用电价
王先生家住丰台区丽新嘉园北区,他告诉记者:“我们小区交房至今已经5年,但电动自行车充电仍按照商业用电价格收取费用。在夜间时段,新能源汽车充电能享受波谷电价,平均充电费用比电动自行车还低。”
据王先生介绍,丽新嘉园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是2019年建成的回迁安置房小区。由于小区土地性质没有变更,小区至今都没能取得房产证。“之前我反映过充电电费高的问题,被告知小区没有房本,无法在供电局系统里进行编号,因此小区公共区域只能按照1.2元/度的商业用电价格进行收费。只有等房产证办下来后,才能申请电箱并更改为民用电。”
丽新嘉园北区共有两栋居民楼,小区配套建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位于1号楼北侧及2号楼南侧。记者在现场扫描充电桩二维码后,弹出的页面显示该处充电桩的电费全天均为1.2元/度,服务费为0.51元/度。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使用该充电桩,充1度电收费均为1.71元。为了进行对比,在小区西南角的广场,记者找到了王先生所说的新能源车充电桩。扫码进入小程序后,记者看到新能源车充电是按照波谷、平峰和高峰三个时段收取电费和服务费。其中波谷时段每度电的电费加上服务费为0.89元、平峰为1.57元、高峰为1.95元。在这三档价格中,只有高峰期比电动自行车充电的价格高。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联系到丽新嘉园工作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丽新嘉园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使用的均为商业用电。根据规定新能源车充电桩可以享受峰谷电价,而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则不存在峰谷电价。“由于暂时没有房本,物业确实无法向供电局申请民用电表及账户,因此现阶段只能提供商业用电。在此过程中我们会要求物业做到明码标价和价费分离。街道方面后续也会继续同电力等部门沟通,看看能否解决电价过高的问题。”
充电价格不透明
混成一笔“糊涂账”
西城区广华轩小区居民近日反映,北京多年前就要求电动自行车充电实行价费分离、明码标价,但时至今日小区内的充电桩仍未执行相关规定,充电价格比其他小区贵上不少,但究竟贵在哪儿却是一笔“糊涂账”。
广华轩小区共有三处充电设施,两处充电桩分别位于小区1号楼、3号楼北侧,小区南门外则是一处充电柜。居民告诉记者,南门外的充电柜虽然做到了价费分离和明码标价,但并非所有车主都能使用,“充电柜只能给锂电池充电,铅酸电池则由于体积过大没法从车上取下,只能使用充电桩充电。”
在3号楼北侧记者看到,这处名为“德康便民充电站”的充电桩共有按充电时长计价和按充电度数计价两种收费标准。其中按时长计价为每3小时1元,按充电度数计价的区域则没有标注价格。扫描充电桩二维码后,记者发现小程序内只提供了按时计费这一种方式。有居民反映,小区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太多,充电桩完全不够用,虽然知道充电桩的计价不合理,但苦于找不到其他充电的地方,只好来此充电。
为验证该处充电桩收费价格是否过高,记者通过小程序找到了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内同为“德康便民充电站”的充电桩。与广华轩小区相比,这里的充电桩旁明确标注了0.51元/度的电费和0.5元/度的服务费。在该充电桩充电1小时后,充电订单显示总计扣费0.2元,电费和服务费各占一半。这一价格的确低于广华轩小区每小时约0.33元的价格。
为何同一品牌的充电桩在不同小区计价规则会有明显差异呢?记者根据充电桩旁的电话联系到了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广华轩小区是高压自管户,电力公司仅负责供电到小区总表,再由小区物业负责将电分配到户。目前物业为充电桩提供的电价为1.1元/度。“现在按照1元3小时的标准来收费,除去电费后相当于我们每度电收0.2元左右的服务费。如果按照电费+服务费来收,现在一般服务费都是0.5元左右,充一度电就要花约1.6元,比现在还贵。之前街道组织开会协调收费问题时我们也去了,但是发现这个小区的充电桩暂时还没法用上民用电,所以只能维持现有的收费标准。”
政策虽然明晰
落地仍有“堵点”
为确保电动自行车充电“不再贵”,确保居民“愿意用、用得起”,近年来本市多个部门陆续发布涉及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标准及运营规范的政策文件及地方标准。
其中,2022年2月,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控的实施方案》,要求充电电费执行政府规定的电价政策,按照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收取,各小区在确定充电设施建设主体时,应明确规范充电服务费收取标准,执行明码标价,确保居民愿意用、用得起。
同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规范本市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充电设施经营单位向用户收取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时,两者应当分别计价、分别收取,不得打包混合收取。居民住宅小区内设置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纳入“居民生活用电”类别,执行政府定价,按照本市“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电价水平执行。
2023年7月,北京市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这一地方标准,其中也明确规定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应公开透明,收费明细应至少包含充电单价、充电量、电费金额、服务费单价等。
今年9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书,进一步重申:实行价费分离,严格明码标价;严格落实相关电价政策,居民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纳入“居民生活用电”类别,按照本市“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电价水平执行。
虽然相关政策规定已经十分明晰,然而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要让定价标准真正落到实处,还需打通充电服务链条上下游的供电企业和设施运营企业之间的“堵点”,属地及职能部门需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让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来源:北京晚报微信公众号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